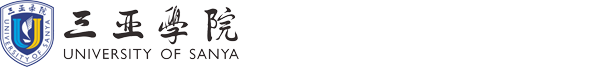文/张跃虎
张宝之
也许可以说,崖州是中国纺织技术的发祥之地。因为没有崖州就没有黄道婆,而没有黄道婆就没有中国古代纺织业的勃兴。提到“衣饰”,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这位在元朝衣被天下的、伟大的纺织技术革新家,和古代崖州人在织技方面的聪明才智。
客语方言把“衣”称为“褡”。“褡”在古代汉语中有两个含义,即:1、小被;见《广韵·合韵》:“褡,小被。”2、衣服破旧;见《集韵·合韵》:“褡,衣敝也。”客语方言的“褡”,很可能是承袭了古汉语“褡”的第二个意思,但在使用过程中去除了“敝”的内含,只用它来指称“衣”了。而在北方的现代汉语中,单独一个“褡”字已无意义;它必须同“包”(或“膊”)、“裢”搭配,分别置于这三个字的前面,才可以构成有意义的双音词。可推想崖州客语群对“衣”的称呼,乃是中原古音在客语方言中的孑遗。这种孑遗,也体现在对“短裤”的称呼上。短裤即长及膝盖的裤子;崖州客语方言称之为“裤?”。古代汉语的“?”指有裆的裤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身自着犊鼻?,与保庸杂作。”足见“?”字的使用可追溯到古远的岁月。现代汉语不再把裤子称为“?”,不知此字在北方是否早就寿终正寝。可它确实还在客语方言中“活”着,只是作为单音词已没有实际意义,必须与“裤”组成双音词,专用于指称短裤。此外,短袖衣有时也被称为“褡?”;但这个词已很少有人提及了。
尽管客语群用于指称衣服的“褡”和“?”源于古代的北方,但其衣着与北方已经没有什么瓜葛,原因是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海南岛最南端,冬天驻留的时间很短,不需要在御寒方面动用太多的脑筋和精力。“褡?”和“裤?”成了普通百姓的常用装束;而这种装束不需要太多的棉布。因此,总的来说,穿衣的问题不会像北方那么突出。
但衣服毕竟是人类的第二张“皮”。而在农耕社会中制作这张“皮”,所必经的周折是工业社会的人无法想象的。把麻种、棉籽与蚕桑变成麻皮、棉花和蚕茧,又变成麻线、面纱和蚕丝,再变成麻布、棉布和绸缎,然后才制成衣服--这一切全靠手工操作,实在太艰难太复杂了。其过程比粮食的生产更费心劳神,更需要技术,也需要更长更多的工序。因此,古人把“衣”摆在“食”、“住”、“行”的前面,除了源于它的象征意义之外,主要还是更多地考虑到了它的来之不易。尽管古崖州的纺织技术曾经独步全国,但这里的百姓要给自己制作一张象样的“皮”,也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
他们不知要付出多少心血与汗水,才能换来一身新衣裳。
日常穿戴
先从崖州客语群的日常穿戴说起。
一方百姓的衣着,与他们所处的地理、气候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笔者一直想弄清楚,客语群的祖先们在南迁过程中的服饰款式如何变化?移居崖州后的衣饰又是什么模样?但由于实物与资料都缺乏,所以一直是一道无法解析的难题。不要说古代的情形已经难以窥探,便是晚近如清末的客语群服饰,能存留下来的也已属凤毛麟角,很难寻找。只是根据所搜集的崖州传统民歌中,倒有几首蕴含着一点这方面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有些混乱甚至相互矛盾,但那几首老崖歌仍很值得珍惜和重视,因为它们多少涉及了崖州客语群历史的服饰和服饰的历史。
下面是两首古旧的摇篮曲(俗称“摇侬歌”);笔者在婴儿时代就听着母亲吟唱,长大后又听她唱着摇大了弟妹。歌词平白如话,不事雕饰,资料性很强:“竹竿打水两边分,崖州水鼎通感恩;藤桥三亚人穿裤,感恩北黎人穿裙。”此中唱到的水鼎、藤桥、三亚,都是崖州故地。感恩、北黎在崖州的西北方向,属于另外的县治地域。所说之“裤”和“裙”,当是女子的服饰。由这首歌可以推想:过去的崖州女子是穿裤不穿裙的。
但另一首“摇侬歌”却又别持一说。它先唱了如何“通(捣)布”,唱了“侬”(晚辈的自称)将把这布“捧”走。接着唱道:“捧去底?捧去后园给母二。缓缓跪下轻轻起,勿作红裙?I草籽。”最后一句唱到“红裙”,似乎崖州女子又曾穿过这种服装。
如果歌中反映的情况属实,也应是很早的事了。“早”到什么时候,则说不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中老年妇女,还有她们的母亲、祖母,都未曾穿过裙。她们把裙子揶揄为“单脚裤”,觉得把两条腿置于一个“裤筒”里是件很别扭的事,那样也容易“春光乍泄”,委实不雅。但近年来,有的进城打工或读书的晚辈把裙子穿回村里,她们也能接受了。新生代的服装款式已是“与时俱进”,五花八门。老一辈也不时接受自己尚可容忍的几款新式衣服,但大体上仍按传统着装。“祖母”级人物的观念相对地更保守一些;她们的装束大多还是老一套。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演进,这些传统服饰已为年轻一代所拒绝,将很快地隐入历史。
裤子。裤子的款式看上去并无男女之别。裤头很宽:可贴着肚皮向左或向右打一个大折,再用裤带拴住。裤带不外是一道麻索或布条:在一头打个死结,卡住一枚方孔钱,再将另一头拦腰绕过来,缠在铜钱上,就把裤子好歹给拴住了。那个油光可鉴的铜钱既是裤带纽,又是装饰品,还是“吉祥物”--所以把它缀在肚皮上,是经过一番考量的。裤裆很长:在里面塞一只猪仔应有足够空间。把裤头往上抽,朝裤带下方一折、一卷,可临时在里头藏些小物件,如槟榔、烟丝、钞票等。其裤筒也很宽松肥大,风一鼓就像两只憋足了气的“天灯”(孔明灯)--此为传统的唐装长裤:老家的客语群称之为“封头裤”。现在,老人都极少穿这种裤子了,故难得一见。最近返乡,想找它拍照,却遍寻未获;后来,叔母才好歹帮笔者问得一件。量其裤头好宽,周长足有1米多,看似为至少300斤以上的大肥佬所特制,但其主人实为一不足百斤的瘦子。
由于“封头裤”同裤带的关系并非那么密切,若不慎而致两相脱离,则有当众露丑之虞。于是,人们后来在它的相关部位来一番改造,把裤带缝进了裤头,并于前面预留出一截带子,以便勒紧腰部。这种“裤”与“带”相连的裤子,名曰“抽头裤”。除“抽头”之外,它的裤裆、裤管与“封头裤”并无太大区别。该款式利于散热通风,与崖州的炎热气候是密切相关的。在盛夏,身着长裤已嫌太热;且它也不便穿下地(特别是水田)去劳动。于是,人们另外设计了一种其长仅及膝盖的短裤,在家或劳动时便穿着它,此即本节开头说过的“裤?”。“裤?”也有“抽头”和“封头”两种:但它同长裤一样,并无明显的男式女式之分。
上衣。两性着装的差别在于上半身。男式上衣被称为“士褡”。大都是“四袋八纽”,对襟;左右前襟的上方、下摆各有口袋两个,下袋比上袋要大得多。襟上八纽均为布料制作:右边一排呈蝌蚪形,套入左排的扣圈。竖领;也有无领的。袖子比较狭,与肥大的裤筒正是大异其趣。有长袖、短袖之别,短袖者即为“褡?”。另有一种男式长衫,竖领,布纽,右侧是开襟;长至脚胫中部,下摆开叉。这是过去的“父兄”才能穿的。
俗称“大钱褡”的女式上衣,款式大体相同,只是袖子有长有短;老式女衣的袖筒很宽,新式的袖筒则也像“士褡”那么狭。纽扣同样是用布制成。右侧开襟;下摆较长。这种设计便于给婴儿哺乳,而蹲下小解时,下摆又刚好遮住屁股。这种衣服,与我们可以经常在影视上看到的清朝女装大致相近。老妇的衣服一般无领,也相对宽松。年轻女子穿的则设有竖领,较为紧身;一些做工精细、讲究的衣服,袖口、襟沿上都饰有美丽的花边。而作为上衣的“附件”,她们的前面还挂着一张类似围裙,但比围裙稍窄而短些的布兜,客语方言称之为“挡幅”。“挡幅”用于遮挡胸腹,颜色大都较深,佩戴者中青年女子;老妇人也有戴它的。姑娘们对它的重视更甚于衣服;她们的挡幅最为艳丽、漂亮,布料与花边都经精心染织,制作上也下足了功夫。在大型的乡村社交活动中,女子们把最美的挡幅挑出来带上,相互攀比、炫耀,或交流制作心得。总之,挡幅成了妇女们衣着的一部分,也是她们最廉价又最重要的装饰品。
笔者推想,“挡幅”的产生首先应是劳动的需要促成的。由于妇女的生产分工(如插秧、割稻等)使她们的前襟容易受到污泥的沾染和谷穗的摩擦,所以弄一块布在前面挡挡颇有必要。久之,这块布就衍化成了今天的“挡幅”。其次,那时没有乳罩;若有奶水渗透衣服,自然很不雅观;有了挡幅,就不会因此而受窘了。再者,“曲线”、“性感”一类今天看来很是“时髦”的东西,在过去却被视为“妖淫”、“浪荡”、“无耻”、“挑逗”;而“挡幅”可起“减震”作用,让封建“父兄”们闭上鸟嘴,也多少增加了自身的安全感。由一张小小的、不起眼的“挡幅”想开去,可知“需要”与“观念”乃是人类一切创造(包括内容和形式)的前提、缘起与依据。现在,生存环境与精神生态的改变已使“挡幅”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所以它也像上面介绍过的旧时服装一样渐渐式微了。
发。崖州客语群女子未婚前留着柳海(客语方言称为“毛掩”),将头发编成一条垂在背后的长辫。完婚即盘成脑后髻,在髻上横贯一支簪(俗称“花通”)。夫人大都缚着头巾。头巾通常染成蓝色,宽约20厘米,长约1米。纵向叠成两层,从前额挽向后脑勺,于发髻的下方打一个活结。也有把整条巾都盘在头上的,但这样的头巾长度就远远不止1米了。记得童年时,邻居有位远嫁崖城的老妇不时回来探亲,她的头上就盘着一条好长好长的黑布巾。她爱嚼槟榔,牙齿都被渍成了黑色;因此把自己的头巾当成槟榔、石灰、蒌叶等物的储藏库,“库”中还有若干钱币。青年女子则较少束这样的头巾;她们对头部的打扮自然要比中老年妇人要认真、复杂得多。如《崖州志》在介绍素馨花时,就说到“闺阁晚妆,摘其蓓蕾,以彩丝穿花心,绕髻为饰,在髻上盛开。见月益光,得人益馥。”又上文引用过的一首传统崖歌,也有“早起梳头讨花插,见花凋零抱花啼”之谓,可见昔时的崖州女子还是颇有情趣的。如果说以素馨“绕髻为饰”只是高雅的大家闺秀所为,则歌中所指“讨花插”的姑娘,当属普通的小家碧玉了。但到了笔者这一代,已看不到类似的状况。“头戴凤冠”、“头插金簪”这一类崖州叙事民歌中时有所述的事像,笔者未曾见识过。盖因这种打扮不仅需要钱,更需要闲情逸致。若竟日为生计奔波劳碌,弄得自己灰头土脸的,也就完全失去打扮的兴趣了。
鞋。由于天气炎热,冬短夏长,故鞋、帽在崖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率很低。平时脚下穿的,多是木屐;头上戴的,多是竹笠。竹笠俗叫“打狗笠”;据称这种笠可用于防狗咬,故名。它以较细的竹篾编成:分里外两层,中间夹着山葵叶,状似天坛祈年殿的圆顶。木屐俗称“山屐”,大都是用质地较为轻、软而便于加工的苦楝木削成。屐后跟与皮鞋后跟相似;屐底其余部分削成一个约120度的钝角。走路时,后跟与角尖触地;屐体沿着钝角的一条边自然地向前倾斜,比穿板凳似的日式木屐省力多了。原始的屐耳用槟榔叶柄包皮或裹着椰子叶柄的那层俗称“椰子布”的黄褐色麻状物制成,到笔者童年时则已改用废弃的汽车内胎。记得那时一双屐的价码是二角五分钱,这对我们而言已是一笔大数目了。
女式鞋有两种。一种只有鞋帮,不包后跟,较为简陋;另一种则是完全的绣鞋,上缀花草,做工很讲究。男式布鞋就没那么精工了。所有的鞋都是平底的,且通常用“椰子布”纳底,以厚布为鞋面。最值得一提的是用牛皮制作的一种简易鞋子,客语方言称之为“皮?”。它不过就是一张脚板大小的牛皮,前端有皮圈套住两个脚趾,另设带子系住脚背、脚后跟。穿上它赶路,既轻便又凉爽。笔者所以特别提到它,是因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皮履》中写到“交趾人足蹑皮履,……以皮为底,而中施一小柱,长寸许,上有骨朵头,以足将指夹之而行。”所言迹近崖州之“皮?”。二者有何联系,颇值得研究。而今,此物已隐入历史,很难见到了。
以上即崖州客语群传统的日常穿戴情况。
大约上世纪初叶,革履、西服始传入州境,被称为“洋装”。革履叫做“革皮公”;洋装上衣称“大扳领”,裤为“洋装库”。客语群将这种舶来品作了“分割”取舍,用其裤而弃其衣。究其原因,笔者想倒不是嫌“红毛番”的“扳领褡”难看,乃是由于普通人买不起它,而它的做工又颇不简单,一般裁缝难以仿制;更重要的是这种上衣并不适合崖州的炎热气候。“革皮公”也出于相同的原因难以推广。洋装裤和西式衬衣却被消化吸纳了;因为它们比较容易服崖州的“水土”,且制作技术不像“扳领”那么复杂,乡村的裁缝经一番学习就能掌握;所以它们得以迅速普及。在笔者的童年即1950年代,村里的“车衣师傅”已能熟练地缝制衬衫和“洋装裤”;该裤式样也有了男、女之分,但衬衫却只有男式的。长度仅及膝盖者称“洋装裤?”;它于上世纪20年代曾在崖州乡间时髦过一阵。这几种“舶来”的衣着形式的受用者照例多是年轻人。它们同传统的“士褡”、“大前褡”、唐装“封头裤”和“抽头裤”一起,构成了一段时期天涯农村日常穿戴的主流。但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之前,穿衣同吃饭一直是严重的问题。国家生产的棉布无法满足需要,只能限量供给。农民们必须自己动手织一些布,以缓解供求的紧张关系。而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他们大都是靠手工的纺织艰难地自己制作衣料的。
那么,这些衣料用何物制成?又有哪几种?
衣料的种类
笔者想把目光投射到历史的更深处,看一看生活在天涯这片土地上的先民是怎样解决穿衣问题的。只是古代的“朱崖州”作为孤悬海外的绝域荒岛,信息很难反馈到中原;它离统治中心又如此遥远,也就勾不起史家们太大的兴趣。相关记载甚少。
《禹贡》有“岛夷卉服”一说。屈大均《广东新语·葛布》做了引述,称:“传曰:岛夷,南海岛上夷也。卉,草也。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之布。”所谓“南海岛上夷”,指的应是海南岛上的黎族先民。若然,则《禹贡》当属最早涉及海南先民衣着状态的古籍了。《史记·货殖列传》写道:“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依注家所指,“布”即“葛布”,是用藤本植物“葛”的茎皮纤维织成的,也即《禹贡》所说的“卉服”。从行文看,织葛布的地域当涵盖儋耳,即海南。《汉书·地理志》(下)把上引太史公的最后那句话照抄过来,接着写到海南先民的服饰,说:“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孙幸任珠崖太守时,因“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贡郡,杀幸”的民变。由引文可知:当时用做衣服的材料有三种,即:一蚕丝织品;二麻织品;三广幅布。如此看来,汉朝儋耳先民的衣料来源,较之《禹贡》产生的战国时期以及司马迁时代要丰富得多。这三种衣料曾在先民们的生活中发挥过自己的作用,但后来却在以“需要”和“可能”为前提的社会选择中各归于殊途,并先后式微、绝迹了。因具体资料较为欠缺,故相关细节已很难查究。笔者从几部古籍中分别找到了若干简单的记载,加上自己的见闻和所作的田野调查,进行一番拼接,由是凑成了这数种衣料从蔚起到消亡的粗略的“路线图”。
先说蚕丝织品。这种衣料,乃是华夏先民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自汉唐始,它就通过海上与陆上的丝路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张美丽而华贵的“名片”。《汉书》说珠崖“女子桑蚕织绩”,可见这里的先民也像中原一样,很早就懂得养蚕抽丝织绸了。据《唐太和上东征传》所记,当鉴真大师于天宝年间东渡日本途中被台风刮到振州(即后来的崖州)时,曾看到这里“一年养蚕八次”。但后来,丝绸的织技与生产却都只兴于岛北,而衰于岛南了。笔者分析,这可能与棉花的传入和在天涯的大面积种植有关。故清初大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棉布》中写道:“崖州多织棉。儋州多织丝。”《崖州志》讲得更明白:“女子不事蚕桑,止织吉贝。”(《风俗》)“……州民只织吉贝,绝少养蚕。间有养者,供作?具,无与纺织之用。黎村养者,能为丝绒。然粗仅备黎裙而已。”(《昆虫类》)在中南民族学院编辑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一书中,笔者也偶在黎族的贸易物品清单上看到“天蚕丝”的名字。可见晚清时期的黎族地区仍有人养蚕抽丝。笔者于1970年代采风中,搜集过一篇黎族民间故事,此中讲到“甘工鸟”如何用“丝绒”做窝,而此窝殊难碰到,会给有幸看见它的人带来好运。足见丝绒的出现已有久远的历史,但一直很稀罕,且被视为神灵之物。诚如前面引文所言,黎胞制作的丝绒仅仅用于刺绣筒裙上的花饰,未曾拿来织造过丝绸。崖州客语群则连蚕都很少养。笔者儿时曾用蓖麻叶养过蚕,但那只是当宠物玩的,与纺织无关。总之,在我们目光所及的历史范围内,天涯住民所使用的衣料中已没有丝绸,只有麻布和棉布。而棉布又有木棉织品与棉花(吉贝)织品之别。
其次说麻织品。从《尚书·禹贡》等古籍的记载,或可肯定麻的使用历史比丝要早些。它也许是从粗陋原始的树皮衣衍化而来,当初不过是简单的披挂物。然后,人们慢慢懂得了将纤维与外皮剥离,使以它编出来的“衣物”更为柔软、舒适;再后才是把纤维掰成丝,织成布,并且学会了种麻。由《汉书·地理志》得知,珠崖、儋耳的古越先民们已经把苎麻视为一种主要的农作物,将它与“禾稻”并列来耕种了。种稻为食、种麻为穿,都是与生存交关的大事。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114条《?子》写道:“邕州左、右江溪峒,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细长为?子。暑衣之,清凉离汗者也。”这里所说的“?子”,或即《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说的“兰干细布”;至少二者是同类。注家称:“兰干,獠言?。”而“獠”即“僚”,是封建文人对黎族先民的一种歧视性的蔑称。笔者分析,黎族呼“草”为“干”,与古代僚人对?麻的叫法相通。上引周文所说的“土人”当为壮族。而壮、黎是同宗共祖的。他们种一样的?麻,应也织相同或相似的布。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葛布》中谈到一种“苎霜布”,又在《蕉布行》一诗中写过“花?白越细无比”的句子,这都与“?子”或“兰干细布”相关。崖州黎族是否也织过此物?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也不好妄下定论。但笔者相信黎族曾织出过上好的麻布,不管这布叫什么名字。而崖州黎族的相关技术,对客语群又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海南与广西的地理气候相仿,所植之麻应即同一品种。《崖州志》“物产”一栏也写到麻,称它有“青、红、白三种。白者为佳。”此中所谓“白者”,可能就是周去非笔下的“苎麻”。笔者在乐东老家也见闻过“青麻”、“坡冥麻”、“厚皮麻”等。其中,“厚皮麻”是从“厚皮树”上剥下的内皮,的确呈红色,该即志书中所指的红麻了。他们都曾被用于织布。但这些麻大都采自山野(笔者向二舅了解过他的剥麻生活),记忆中也有人工种的“青麻”,可是为数不多。或许是因为人口日增、耕地日缺的缘故,《汉书》上说过的,大量种植苎麻的生产生活不知何时已趋渐停滞。然而麻的需求量仍然较大,野生麻数量又有限,于是从岛外购进一部分,是谓“精麻”或“青蓝麻”。1950年代中,童年的笔者仍见过此物,朦胧记得它呈黄褐色,像一捆捆干柴。因无相关资料,不知“精麻”是何时上岛的。据笔者的调查对象二舅植生公等人的回忆,它的售价是8分钱一斤。1960年代之后,它才渐渐销声匿迹。除此之外,在其它地方亦有取菠萝叶中的白色纤维织布者,称“波罗麻布”。《儋县志》说它“所在皆有之……其出定安、文昌者犹佳。细者如轻绡雾?。”但《崖州志》并无类似记载。童年时,笔者见过大人这样剥取过菠萝叶中的纤维:先把它割下,在水中沤烂;取出,用圆滑的碗口边沿慢慢刮去已烂的肉质部分,剩下的就是白色的纤维了。但此物似是被少量地拿来掺在棉纱里发挥有限作用的,未曾看到专门以它制作的织品。屈大均所说“出琼山、澄迈、临高、乐会”的、“轻而细”的“美人葛”,以及“蕉布”、“竹布”等,在崖州也都不曾留下什么痕迹。
笔者虽无缘见识“蕉布”,但对用于制作蕉布的蕉麻,却十分熟悉。小时候,常从芭蕉茎上把它剥下,接成长长的绳子,拿来放风筝。其纤维远不如“厚皮麻”坚韧,也不似“波罗麻”洁白,但它量多、易采。因此,很早就成了中国南方先民们重要的衣料来源之一。西晋人稽含《南方草木状》(上)说到:“此(甘蔗)有三种:……种大如藕……其茎解散如丝,以灰练之,可纺绩为??,谓之蕉葛。”同时代的左思(约250—约305)在《吴都赋》中也写到“蕉葛升越,弱于罗纨。”两文中之“蕉葛”,皆为布类;因源自蕉麻,质地较次,故远不如罗纨之耐用。从蕉麻到蕉布,首先要经过一道工序,即稽文所说的“以灰练之”。清人李调元在《南越笔记》(五)中进一步说明:“……以蕉身熟踏之,煮以纯灰水,漂?萘罡桑?酥??肌!苯幼庞种赋觯骸肮闳似闹亟恫迹?龈咭?⒈Σ椤⒐憷?却逭哂让馈!绷碛凶柿媳砻鳎?=ㄈ艘灿谩盎伊贰敝?ǎ??堵榧庸こ伤柯埔灾?肌?梢酝葡耄?魑?=ㄒ泼穸?志佑谠?愣?厍?难轮菘陀锶海?欣碛伞⒂刑跫?龉?庋?氖隆L剖?似と招菰?从小吧?溆胪掺。?瞬坏浣兑隆钡木渥印?杉?堵橹?贾埔轮?伲?诠糯?哪戏皆??跷?毡椤V皇谴耸略谘轮莼估床患暗巧现臼椋?敖恫肌币丫?弧凹?床肌碧蕴?恕?/span>
再次是广幅布。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葛布》中说:“古时无木棉,皆以细麻为布。惟粤之苎则自上古已有。”此说在中原一带当然不错。但就木棉花漫山遍野的海南而言,这种说法就不确了。
在海南,木棉布的制作历史或许同对麻的利用一样悠久。木棉也叫红棉、英雄树、攀枝花。而笔者故乡的老百姓则习惯称它“芒棉”。它是一种大乔木,早春时节叶已落尽,满树花开;花有碗口般大,颜色淡黄或深红,极之艳丽。在海南岛中、南部的山区或半山区长势尤旺,常相拥成片;春节前后,但见树树凝焰烛天,山山云蒸霞蔚,非常壮观。它的木质较软,或许是为了自卫,树皮上便突起许多方孔钱大小的尖硬疙瘩,俗称“芒棉钉”;因为此“钉”质地较轻又不易变形,乡人常取它雕成鸽哨的进气口。果实呈香蕉状,干后开裂,中有棉絮。专家们都认定其“纤维无拈曲,不能纺纱。”《辞海》相关条目即持此结论。屈大均《广东新语·木棉》也说它“脆不坚韧。可絮而不可织。”在通常情况下,上述说法都对。但海南岛的黎族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他们确实是以简单的纺锤将木棉絮纺成了纱,并织成了布。这种布洁白、保暖,还能防水。笔者推想,《后汉书》上所说的“广幅布”,应是用纯木棉纤维或用它再加上苎麻纤维织成的。这种制作工艺延续了近两千年。直到1950年代,以木面纱混着麻线织成的黎被还温暖过笔者的童年。既可为被,自然亦可为衣。《崖州志·花类》也写道:“木棉花……老则折裂,有絮茸茸。黎人取以作衣、被。”该志书的编篡者与黎胞同处一州,其记载是可信的。在衣、被方面,崖州客语群曾多年受惠于黎胞,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是曾经盖着黎被过冬的。
好多古籍,甚至包括海南本地的古籍都把木棉混同于“吉贝”,进而混同于陆地棉或海岛棉。如《儋县志·木帛类》云:“吉贝布,系纫木棉花絮所织者。”而《崖州志·花类》则认为“木棉花,有二种。”并把“吉贝”归为其中之一种。其实,木棉与吉贝是两码事,不可相淆。木棉乃“土著”,大都是野生的。吉贝则是从南亚传入的陆地棉或海岛棉,即普遍所指的“棉花”,而“吉贝”是它最早的名称的译音。但究竟是译自梵语、柬埔寨语还是马来语,则诸说不一,无从考辨。笔者认为,棉花应是首先在崖州(古振州)登陆,然后才逐渐北上,并渐渐向大陆内地扩散开来的。理由有四:一是崖州客语群一直称棉花为“吉贝”,到现在还是这么叫。只是“吉”的发音近乎“gei”,类似粤语;而“贝”的发音则近乎“bua”,这又是纯粹的崖州客语方言。对棉花这个古译名的保留,表明它初次登陆时的最可能的地点应当是这里。二是从地缘上看,崖州的地理、气候最接近南亚;它又同南亚一样,是从中国泉州通向阿拉伯的海上丝路的必经之地。因此,它自然就成了接纳南亚“客迁”植物最方便最理想的平台。三是古崖州的棉花纺织技术曾一度领先全国。中国的其他地方--包括海南的另外几个州--都与伟大的织技革新家黄道婆无缘,而她偏偏出自崖州,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肯定:当中国其他地方都还在探索着如何把“吉贝”这种新奇玩艺变成布料的时候,最先接触它的亚洲人已在相关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并以此哺育了黄道婆,从她带到上海的纺织技术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可以推断,当时,文化昌明的长江三角洲在这方面要比偏远蛮荒的天涯崖州落后得多;其他地区的差距更可想而知了。四是崖州的前身--古振州本来有发达的蚕丝业(“一年养蚕八次”),但此业不久就比其他地方更早地销声匿迹,若不是棉花最先造成的冲击,何至于使天涯人这么早就放弃蚕桑?
又,明朝中叶的琼州籍大学者、大政治家兼经济学家丘?F(1421—1495)曾晚年写过《吉贝》一诗(见《四库全书》收录之《重编琼台稿》):“吉贝传从海上来,性尤温暖易栽培。富贫贵贱皆资赖,功比桑麻更倍哉。”此诗秉持丘公特有的风格,讲的都是些大白话、大实话,写到了棉花的来历、特性和比“桑麻”更大的功用。它对丝、麻织品的淘汰,也已被对中国经济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的丘公注意到了。
那么,它“传从海上来”的时间,始于何年?笔者认为应是唐朝。因为从那时起,“吉贝”和讹传的“古贝”这两个词,就频繁地出现在中原的古籍中了。北宋苏东坡流放儋耳,某日黄昏与一陌生而豪爽的山民邂逅于市井,并接受了对方馈赠的衣料;苏公有诗(《和拟古九首》之九)记其事,最后两句是:“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可见当时的海南人早已用棉花来织布。比邱浚晚生54年的崖州籍大学者钟芳作《珠崖杂兴》,其中也有“山下小园收吉贝”的句子,苏、钟二人,一个流放本地,一个土生土长,应知棉花(吉贝)与木棉花的区别。钟诗中的“山下小园”当为人工开辟,显然不是野生的、高大的木棉所待的地方。也没有人会愚蠢到动用宝贵的园地,来栽种随处都可以采到的木棉。因中原人士隔山隔海,孤岛的信息又如此闭塞,以至于许多人都把吉贝、木棉都混为一谈了。这种谬误又“出口转内销”,倒过来整“晕”了海南本地的文人,他们也就跟着以讹传讹。还是在广西实地考察过的周去非比较明白。他在《岭外代答》117则“吉贝”中所描述的,正是棉花:“吉贝木如低小桑,枝萼类芙蓉,花之心叶皆细茸,絮长半寸许,宛如柳绵,有黑子数十。……以之为布,最为坚善。”还特别赞赏“南海黎峒”所织的吉贝布“幅极阔”,“间以五采,异纹炳然”、“五色鲜明”等等。可知经过了唐代与北宋的长期的技术准备,到了周去非所处的南宋时,海南黎族先民纺织吉贝(棉花)的工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总之,海南传统的衣料有四种,即:蚕丝、麻、木棉和棉花(吉贝)。但在崖州,缫丝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就已经停滞并消亡了。后三种植物成了崖州人衣料的主要来源。不过,根据笔者的调查,客语群并不使用过木棉,也未曾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因为他们迁入崖州时,这里早就引进比木棉优越得多的“吉贝”(棉花)了。用于织布的棉花,大都是自己种植的。在笔者所搜集的传统崖歌中,就有“上岭劈园”,向荒野伸手。钟芳诗“山下小园收吉贝”,大体上也是这意思。这“吉祥宝贝”在荒寂中与天涯农民相伴了漫长的岁月,直到鸦片战争后大量的洋纱拥入海南,被称为“西洋白”的洋布也源源不绝地随之而来,它的种植才渐渐萎缩了。建国后,国产的棉纱和布匹渐多,而海南的耕地又很紧缺,且时有粮荒;只要可以买到布和纱,则再种棉花已无必要。于是,“吉贝”在这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它曾经藉以落脚的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