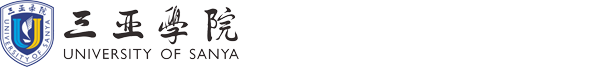译介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启示
刘伟
[摘要] 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支,不同于狭义的翻译研究,更是一种在文化翻译背景下的对翻译文化的考察。译介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启示包括: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性质;重新定位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其中非母语写作现象的归属;开拓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的范畴等。
[关键词] 译介学;少数民族文学;非母语写作
译介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门类,属于比较文学的一支。译介学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也就是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语言研究的藩篱。用谢天振教授的话说:“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译介学所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而是属于一种文化研究范畴,研究“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译介学研究的是文学之间的转换以及转换背后的运作机制,这种转换当然不止是简单意义上的“语际翻译”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同样还包含了雅各布森所谓的作为“重述”的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以及作为“变形”的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正是译介学这种宏阔的研究视野为我们进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启示。
一、译介学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学的性质
译介学之所以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所启示,就在于少数民族文学本身也具有某种翻译性。而这种翻译性,并不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转换层面,更是背后的文化间性的体现。由于民族的边界和文化的边界很多时候是重合的,那么民族文学的写作和交流,在全球化时代,往往表露出一种跨文化性。不管是在语言层面、内容层面后者是作品的精神层面,总会呈现一种文化的混杂性(Hybridity)。
具体说来,由于民族的差异以语言的差异为典型的表征(当然语言的差异并不是民族的真正区分原则),那么同样,语言亦成为民族文学差异的症候。这里并不是说民族文学就是以语言作为边界,但不同的民族文学之间必然存在语言上的(广义的语言,包括语言符号本身,以及表达的方式和手段)不一致。正因为民族将文化和语言作为自身的标志之一,那么跨越民族边界的写作或者交流活动,某种程度上也是跨文化和跨语言的,而这正是进入了翻译的范畴。同时全球化时代,最为典型的并不是写作的跨文化性,而是阅读的全球性。民族文学的生产,在现代传播技术的作用下,可以迅速超越民族界限,而被其他民族所了解(虽然不是纯粹的理解)。虽然,这其中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就像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所说的受着文学内部的原则比如“诗学形态”(poetics)和文学外部原则诸如 “赞助人”(patronage)和“意识形态”(ideology)重重制约,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学作品都能实现对民族边界的快速跨越,而被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所“前景化”(foregrounding),进入主流文学系统的“形式库”,而这往往也意味着它获得了“经典化”的先机。但即使如此,我们不能否认至少在传媒技术上,全球化时代已经实现了对民族边界、国家边界、文化边界乃至文学边界的跨越。比文学传播速度还快的读者反馈机制和极大化的文化市场,使得文学写作获得了某种方向性。在全球化时代,文学被生产出来,不再将文学性为基础的分类(比如雅/俗,优/劣)作为标准,而是以阅读对象来分类:是写给本民族读者的,还是写给其他民族读者的,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对于全球性的受众群体,文学的写作不得不在“异化”和“归化”策略中作出选择,或者干脆在两种策略中来回穿插,摇摆不定。而这正是民族文学——这种民族文学并不是狭义的,那种纯粹的、地方性的、小写的、本民族的文学形式,而是指广义的、大写的文学。之所以被称为民族文学,不过是作家本身具有民族身份,而这种民族身份也只是作家众多身份中的一种,也并不一定被主动嵌入其文学作品之中——混杂性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