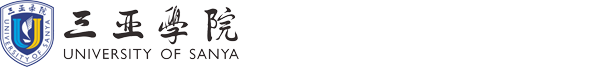文/张跃虎 张宝之
棉纱的加工与野麻的采集
不管是棉还是麻,将它们变成布料都颇不容易。此中要经过复杂的工序和繁重的劳作;而对于农耕社会来说,这个过程的技术含量还相当高。 先从棉花说起。 把棉絮搓拧成丝,这是向布转换的第一道工序。笔者未能看到上一辈客语群妇女把棉花纤维纺织成纱的过程,因为懂事的时候,现成的棉纱已大量进入汉区了,但多次见过黎女捻纱织裙。直至1983年被调离五指山区,去《海南日报》工作之前,笔者还经常可以看到黎家嫂子在凤尾竹或椰树下进行这项作业的情景。 黎胞捻纱的用具很简单,记得主要部件就是一支约六寸长、筷子头粗、下端削尖的圆形实心竹签,和一枚拦腰紧箍在竹签上的方孔铜钱。铜钱离竹签的上端约寸许。抽纱时,先把棉花拈成一段细线,作为纱头拴在竹签上端,并拎在手里;然后两只脚板并拢,把铜钱下方的那截竹签夹紧,各朝反方向使劲一搓,使竹签与铜钱相互作用、悬空旋转,同时不断抽动拴在竹签上端的棉丝;手中那团棉花便像变魔术似的越扯越长,长到接近了手的活动边界时,已变成一条均匀的细纱。这才把它收起,缠绕在竹签上。笔者所看到的这种抽纱方式,属于远古的原始纺技的孑遗。竹签上的铜钱所起的乃是纺轮的作用;而纺轮远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出现,但那时多的是陶制,也有少量以石制成。有了铜钱,它们才被淘汰了。 崖州客语群或许也曾采用过这种拈线的古法,但在建国之前,现成的面纱已率先在汉区逐步结束了以人手加工棉花的历史。不过那时的纱也不是可以轻易得到的,直至1950年代初,它仍然是非常贵重的东西,所以成了迎娶新娘时最有脸面的重头聘礼。笔者童年时见过的纱捆被扎成方形,约有尺许长。有关它的那些细节都颇有史料价值和民俗研究价值,但未曾见诸任何记载。因此,应该详细地写一写,否则相关资料将被岁月完全抹去,而笔者的调查对象正是故乡昔日的“织女”,她们提供的材料不仅有趣而且可信。 客语方言称棉纱不是以“捆”而是以“股”为基本单位,每股纱由12“练”组成。所谓“练”,也就是盘成了圈后又垂为条状的一大把纱缕,这纱缕扯直了长可尺余。“练”也是客语方言音,字照例是笔者“兑”出来的。“练”,也作“??”,含义之一是水煮丝麻或布帛,以使之更为柔软、洁白。《周礼·天官·染人》曰:“凡染,春暴练。”按郑玄的注解,“暴练”即“练其素而暴之”。此中的“练”与客语方言的“练”当然不是一回事,但二者都与“布”相关,所以笔者选了此字,每“练”纱重一斤,所以一“股”纱的重量通常是12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十二斤棉纱的价钱高达300元“国币”(而当时崖县县长的月薪不过70多元;也就是说,他4个月的薪水才够买一股纱)。随着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后来才降至80至90元。 把纱买来后,先用水泡“一个对时”(24小时),再一一松开被捆实了的纱缕,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水和一斤半白米,煮上两三个钟头,直至把米煮到烂熟。将纱同烂米一并捞出,置之簸箕,使劲搓揉,尽可能把烂米揉进纱里。然后是浣纱。专作此用的是一个很大的陶盆,本地方言称之为“拍纱盆”。煮纱与浣纱,已有悠久的历史,词牌《浣溪沙》,想来或许是错的,似应为《浣纱溪》。客语群所居之地也有溪流,但不多;大都只能以“拍纱盆”代之。在此扯上一点和纱有关的“古”,自非无的放矢。在下文写的“捣衣”时,读者还会看到:唐代诗人笔下的相关场景,而客语群的妇女们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这是中国农耕社会特有的“诗意”之美--但却是无奈的美。 浣净纱缕,抖掉多余的米粒,将纱缕串在竹竿上晒干,就可以“规纱”了。“规纱”,又是一个客语方言词,指的是把经过初步处理的棉纱缠上一个用竹篾编成、有手臂般粗、长约一尺的圆形竹器。这竹器被称为“规赉”,它固定在一个摇柄上:转动摇柄,它也随之旋转。小时见过“规纱”,通常是两个人配合:一人双手撑开纱圈,另一人则在数尺开外摇动“规赉”,把纱绕上其腰身。撑纱不需要什么技术,所以谁都可胜任。掌控“规赉”者则必须是拥有一定经验的妇人。因为她得把纱线缠得尽可能均匀,还要随时关注着纱线的质量,将断掉或欲断未断的纱重新接牢,同时又不能有太大的线头,否则会影响成布的质量。 下一步是更为讲究技术的“牵纱”(也叫“牵布”)了。这项作业要在已清理干净的平地上进行。先在地上打桩;准备织几匹布,就打几对桩。一股纱通常可织8匹布,故用桩16支。这些桩分两行平行相对而立,每行8支;行距3丈;桩距5寸;它们露在地面的高度也是5寸。两行桩的正前方架起一块宽约5寸、厚3至4分、长7至8尺的木板。板上并列着12个圆孔(但通常只有8个),孔距3至4寸。此件俗称“出纱板”。板的下方地面一字儿摆着8个已缠满棉纱的“规赉”,它们各各正对着一个出纱。牵纱者共仅3人:一位师傅,两个工仔(徒弟)。每个“规赉”上都有一条纱穿过出纱孔,且全被师傅揽着:他不断地两头走动,分别将纱递给各守一行纱桩的工仔。工仔就按照师傅的要求,顺序把纱挂到木桩上。“牵”完一股纱,用梳子从头到尾把纱认真地梳理一过,才开始“装规”。 所谓“规”,即“布规”,此乃客语方言对脚踏织布机的称呼。这种织机有可能是黄道婆时代的古老遗物,但对于农耕社会而言,它的构造与原理还是相当复杂的。由于已废多年,它所占空间又大,没人愿意完整地保留着它,所以在农民家中已无法找到。笔者后来在东方市某小镇寻访到它的踪影,可收藏者却不许拍照,所以读者看不到它的直观形象。走访过的调查对象虽然织过不少布,但并非装规师傅,且表达能力有限,很难准确地描述“规”的结构及装规的步骤与过程。而熟悉此道的人已经老去或逝世,相关知识也就派不上用场,也许自此永远失传了。从笔者1976年岁末采录的崖州民歌《织女叹》中,可知“布规”的一些重要部件:如“两支吊连锁相关”的“布单”,“纱屈千层在中央”的“布梭”,“怨纱千条割不尽”的“布刀”,和“双对双”的“靠框”等。但怎样“装规”仍无从知晓。只知这比牵布、织布都要烦难得多,也“技术”得多。熟练者至少需一整天,不熟练则要两三天,才能装好。 然后,更枯燥、乏味、艰辛、漫长的织布过程才就此开始。 用麻线织布的工序、要求及具体作法,和棉织品略有区别,但基本环节大致相同。先了解一下麻的种类和它们的采集加工情况。 崖州客语群用于织布的麻可归为两类。一类是从岛外购入的青麻和蓝麻,即“精麻”;另一类则是本地的野生麻。这一点,上文已有所交代,这里需要略作补充的是对精麻的处理。这种以8分钱一斤买来的麻,其实还带着树皮。故使用时得先放在大锅里用水煮过,沤烂表皮,揉出皮渣,泡软纤维,撕成丝,纺成纱,掺在棉纱中织成浅黄色的布。而煮麻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作法,笔者读《诗经》时,注意到有好几篇涉及“葛”的古歌,其中的《葛覃》还直接吟到煮麻:“是刈是?C,为?为?”。“?C”就是“煮”的意思。崖州的野生麻则主要有两种,即“坡冥麻”和“厚皮麻”。前者最高可有两三米,粗如人腿。但这样的树已经太老,皮都粘在干上了,很难剥,砍起来也费劲,所以人们不会找它。选用的都是些拇指大小的幼树--它们喜欢一丛丛簇拥生长;只需砍下几丛就得到一大捆,可扛到阴凉处,慢慢剥皮。黎胞用于织裙、织被的,主要是这种麻,其制作工序与精麻略似:也是先把剥下的麻皮放在大锅里煮过,又置于溪流或水塘中泡上七八天,将皮泡烂,然后抠出来漂洗,脱尽皮屑,再将剩下的纤维晒干,撕捻成线,以比汉族的布规简单得多、可随时卷起带走的织具,织成穿、盖用品。一些麻织品(如黎被)还参有木棉。黎被由五幅宽1尺、长6尺、带花纹的麻布拼缝而成,时价是一张五至六元。 崖州客语群也有人用“坡冥麻”,但较为常用的还是取自厚皮树的“厚皮麻”。它也是一种小乔木,但树不分老幼皆可采麻;且树皮不粘树干,容易采集加工。其纤维甚为韧长,用途也很广:不但可以织布,还能绞成各种农家用绳,如牛索、车索等。直至笔者的少年时代,还看到故乡的农家大都在檐下挂有此物,以备不时之需。但它这时已不再被拿来织布,而只用于制绳索、捆东西了。可是在建国前夕,厚皮麻仍是布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剥麻皮”也便成了一项收入颇为可观的家庭副业。当时,一斤晒干的“厚皮麻”可卖三个铜板。一个能干的农民一天能剥50斤湿麻,晒干了剩余20斤,尚能卖60个铜板。但这样的能人极少。普通农民只能剥到三四十斤,晒成十几斤的干麻。当然,采麻也是很辛苦的。笔者二舅符值生年轻时曾干过这营生;他回忆了自己当年采麻的一些细节: 鸡初啼,天不亮,剥麻人就得起来准备了。需要带上的东西有:一把山刀,一个“?包”,一双拖鞋。后两样东西都是用槟榔叶柄的包皮制作的:此物俗称“槟榔皮”,是崖州农家多种用具的最方便也最廉价的原料。“?包”里裹着刚做好的干饭。拖鞋以同样的材料折叠而成,俗称“槟榔皮?”,有好几层,比脚掌略大,前端尖,后跟平。“人”字形的鞋耳也是用槟榔皮编成的。一双这样的“鞋”可穿一个月。采麻人把它挟在胳肢窝里,到干活的地方才穿。光脚徒步十几里,进山后,先选定一个落脚点。该“点”必须有较多的厚皮树,还要有水,以便渴时饮。在此要藏好?包,并用荆剌严加封护,以防乌鸦扒开、偷吃。把整株砍下的许多厚皮树干全都搬到阴凉处,就可以开剥了。顾名思义,这种树有很厚的外皮;纤维在皮下,与表皮互不参插,所以不必像对付坡冥麻那样又煮又泡,就可以将纤维剥离。其树粗生速长;老树高可六、七米,主干粗于人腿。但木质较软,纹理又直,劈开不难。剥麻时,先把较粗的树干开成四爿,细的开成两爿。继而剥下树皮,再从皮上剥出纤维。纤维里水分很多,必须即时集成一束,把水拧干,否则它晒过后会变得很硬。将附近的厚皮树砍光剥尽,把剥下的麻纤维就地挂晾在用三脚架横着架起的木条上,再转点劳作。一天只能换两三个地方,日头欲落时,把分晒几处的麻收拢到一起,捆成两捆,砍条圆棍削尖了两头,串起麻捆挑回家------ 这就是剥麻人一天劳动的生活速写。他也许得连续十天半月这样干,日日早出晚归,不断变更剥麻地点。所有挑回的麻都还得继续晒到干透,然后或者出售,或者自用。若用于织布,则先要把麻条撕成细丝,并连接起来。接好的丝线放在藤萝里,蓬松一大堆,都是一条线。但须小心管好线头,以免都纠缠到一起。倘若两只打架的狗捣翻了麻篮,搅乱了麻丝,则整理这东西真会“烦”死主妇。笔者由此想到:所谓“麻烦”、“麻沸”、“事多如麻”、“心乱如麻”、“一团乱麻”、“快刀斩乱麻”等成语或熟语,或许就是我们的祖宗面对着这些麻丝体悟出来的。 麻丝可散而不可乱。将接好的丝纺成麻线,就可以绕过“牵纱”这道工序,直接“装规”织布了。 织染与捣布:衣料的完成 机杼声声,在文人听来是颇有诗意的。“男耕女织”的现实描述,“牛郎织女”的虚幻故事,“天女织云”的奇思妙想,都把织布的劳作诗化了。但在村妇的眼睛里,这些活却一点也不浪漫,更不轻松。 崖州客语群妇女绝大多数都会织布,笔者祖母就是个远近闻名的装规(机)、织布能手;她织出的“斜纹布”、“花仔布”,一上市就会被抢光。她人固聪慧,但这种技艺也是生活逼出来的。到了母亲这一辈人,生存压力有所减轻,织技也就随之减色。她与她的同辈妇女,已经织不出祖母曾经织过的亮丽花纹,更织不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绵布》中记述过的“绣人物花鸟其上”、“十金一具”的“崖(州)帐”了。但织布的辛苦则一以贯之。由于白天要下地干活,所以这项劳作往往是在夜间进行的。电灯直至1960年代还是天涯乡村的神话,而1950年代则还普遍使用昏暗的海棠油灯:晚上,如豆的灯花轻轻地跳荡着摇曳着,将昏黄惨淡的微光无力地抹上布规。笔者记忆中,布规的前后都有两根纵向平行伸出的、相距约近两尺的把手,应是预备抬动这大家伙时用的。在把手上横架一块长条木板(这木板常常就是番薯刨),便成为织布人的坐具了。此物宽不过15厘米,又没有什么扶手和靠背;它给使用者造成的不舒服,可想而知。 母亲就坐在坚硬的薯刨上,穿一件补丁压着补丁的衣服,把“布刀”从右边平伸入两层轻纱的夹缝,让左手也勾住“刀”的另一端,两手均匀使力,用“刀刃”砸紧刚牵入的纬线;再把横串于轻纱上的、齿缝十分细密的“布梳”拉过来,在布口的纬线上撞两下。同时踩一踩脚下的吊杆(“布担”),使交错的经纱互换上下位置,又从左向右伸过布刀------日复一日,母亲就这样不断地、机械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她还必须十分留心,努力不要让布刀串了纱,或碰断一条经线。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发髻上总插着一支尾端粘有蜡团的豪猪剌。剌尖可帮忙检查并挑出断纱;接纱时有它相助,可使接头的余线尽可能短些。蜡团则用于将起毛的棉纱粘紧。母亲那佝偻着的、瘦小的身躯,在微茫的昏灯下不断地一俯一仰;单薄的肩膀,随着织布的动作轻轻颤动。吊杆?G乃,布刀卜卜;乏味的响声中,棉布以数秒钟半毫米的速度缓慢地、又十分顽强地向前延伸。千百年来,天涯崖州的村姑和母亲们,还有乡土中国无数的村姑和母亲们,就这样辛勤地在布规上编织着温暖的梦--为了家庭,为了丈夫和孩子。 棉布在单调的机杼声中铢积寸累,终于成匹了,但它也只是粗糙的布料,还不是衣料。下面仍有一个繁杂的工序:染。 染料,完全是自制的。所用原料为草类植物,《崖州志》是这样介绍它的:“蓝草,有数种。曰蓼蓝、菘蓝、马蓝、吴蓝,皆可作靛染衣。又有木蓝,高三四尺,分枝布叶如槐。七月开淡红花,结子长寸许,与诸蓝异,而为靛则一。黎村多此种。军语名为茜。”把“蓝”的种类区分得如此之细,可见编纂者是作过相关调查的。但乡间百姓--至少笔者老家的农民--似乎不想弄出那么多名堂,他们将用于靛染的植物都叫做“青”。童年时代,笔者跟着母亲到村边小园去种过“青”。记得那时暮春雨后,空气很清新。母亲在园中撒下青种,用铁搭轻扒一过,就完事了。笔者见过并留在印象里的青,似如《崖州志》所写的“木蓝”,但是否“开淡红花”则记不真切了。在笔者的田野调查笔记中,“青”应是下种三个月后收获,时间是农历六月。它的成色、价钱等与市场关系较密切的部分,这里暂不详述,只说说关乎“靛染”的内容。 染料制作的简略过程是这样的:将刚砍回的“青”去其主干,留其枝叶,折成手臂大小、一尺余长、并即以其枝拦腰扎牢的青捆。把这些青捆纳入一个高约1米、口径约40厘米的大腹染缸,一层层尽量压紧,最后在表面镇以重石,防止其上浮。接着倒进清水,刚可把青捆浸没。阖上缸盖泡三个昼夜,谓之“发缸靛”。第四日开缸,将叶已全烂、只剩光枝的青捆(这时应称之为“渣”了)取出,剩下已经上了色的半成品染料。再兑入两大盆“齑”。这里所用的“齑”与用于煮干薯汤的“齑”略有区别--拿来滤水的,除了草木灰(占八成)之外,还有石灰(占两成)。 兑齑之后,即用干竹枝捆成的“青砸”使劲搅动,这叫“拍缸靛”。一直搅到靛水沸起许多白沫,乃加盖,不再动它。又过三天,才把缸盖移开一条缝,抓一块白布浸入靛中不断捏拿,取出检查够不够成色。倘嫌不够,就到镇上买回两斤凝固的“缸靛底”溶进去,并再搅拌一次,直至泛沫如沸为止。隔一夜复检,作法如昨。若还不满意,可续加“缸靛底”。不过,通常只需加料一次,便可使用了。 制作“缸靛”可不是一件小事。弄不好把它发“白”了,既伤神与破财,又耗时与费事,还不知预兆着什么舛运。因此只许成功,不可失败。但总是有人失败过,并且由此想象出种种莫名其妙的古怪原因,于是产生了种种莫名其妙的古怪禁忌。如,“缸靛”通常放在“鸡翅”(厅外“檐沟”的两翼)里。又如,“发缸靛”的当天,要在这里最醒目的地方挂一蓬树叶,是谓“打星”,以提示他人不要在此“乱说乱动”,特别是“带孝人”(新近有亲人逝世者)、“四目人”(孕妇)更不可靠近,且绝不能触摸靛缸。这两种人看到“鸡翅”里的“星”也会主动回避。若有什么事要找女主人,也只能托邻居传话,或把她请出去谈,直到把缸靛确定无疑地“发”好,主妇悬空的心才放了下来,家人也陪着她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开始染布了,禁忌随之解除。 染布的第一道工序,客语方言叫“捏缸靛”。这个词虽然“土”,但还比较贴切。“捏”法是:侧坐在染缸旁的板凳上,欹着身,把织好的白布挂搭于缸口的边缘,将它的一侧浸入靛中,然后逐寸捏拿:一只手不停地一抓一放,一紧一松;右手累了,就换左手。双手轮流换作,缸靛便在捏拿中不断发出有节奏的“渍、渍”之声。染料则一点点随声渗入布,使之渐渐由白变蓝。捏好了一截,再放入一截。同纺纱、牵纱、织布一样,靛染也是由女人干的。这比织布还枯燥乏味。且染布的同时,双手也被染成了蓝色,两三个月都没法褪去。此活看起来粗放,实际上有颇高的技术含量。因为女人无法看到自己在捏的布,所以色调是否均匀和统一,及与此相关的“捏拿”的力度怎样把握,全凭手感、经验和直觉。新手很可能把布捏染得青一块白一块,或浅一块深一块。这时,就要靠有经验的老妇来补救了。 为了赶时间,女人们有时会彻夜劳作,“渍渍”的脆响便如同单调的节拍声,伴着夜虫的清歌响到月沉。但夜里靛染的多是些不关紧要的东西,比如头巾及褪了色或打了不同补丁的旧衣服等。而给新布上色则大都在白天进行,因为白天才能检测和评估染色的质量,找出毛病并及时纠正。又布匹一日要分三次上色:捏拿一过后,在竹竿上晾到半干;复捏复晾,如是再三,才算初步完成靛染。染布人根据自己和家人的意愿与需要来控制颜色:若要其黑,则捏时用力些、久些;倘欲其青,则捏轻些,时间短些。通常半缸染料只能染两三匹布(每匹布3丈长、1尺宽),用个十天八天。这时,缸中的颜料都已染在布上,靛水也开始发臭,该把它倒掉了。“捏”过“缸靛”,还要“上色”。所“上”的“色”通常只有三种:红、青、黑。 红色的制法是:用一种俗名“树胶”的树皮同“厚皮树”的树皮混在一起,放入体高腹深的陶罐(俗称“深肚罐”)和水煮之,可获红色染料。再撒入适量薯粉,以增其浓度。将染料一点点分批倒进木质脚盆;倒一点,让“缸靛布”吸纳一点,不使浪费,力求均匀。浆染一过,晾干,像“捏缸靛”一样重复三遍。因底色已是靛蓝,再这么一染,便成了暗红色了。 青色的制法是:将挖来的山稔子(客语称之“娜妮”)的根部洗净,刮起皮,置于“深肚罐”加水煎;将水倒出,溶入一种名曰“一品莲”的固体燃料;染法同上。 黑色则是用晒干的牛皮烧去毛,切块煮烂,以此水直接浆染(不必再撒薯粉),也染三次。这样,布料的染色工艺始告完成。如此浆染,一举两得:既丰富了布料的色彩,又使它更加结实耐用。另外,在1950年代,童年的笔者也见过祖父把废弃的电池中的炭粉收集起来,调之以水,把布染成灰色。但这是一种“另类染法”,似与传统无关。 让布成为衣料的最后一道工序,便是颇具诗意的“捣衣”了。 唐诗中颇有些叙写捣衣的精彩之作,如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杜甫的《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宁辞捣衣倦,一寄塞垣深。”有论者以为诗人写的是洗涤和拍打衣服,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先师黄雨先生《新评唐诗三百首》解得好:“所谓捣衣,其实是捣布;即把织好的布帛放在石砧上用杵捣击,使之软熟,以便缝制棉衣。”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以此为题材的唐诗,还有钱起所作之《乐游原晴望上中书李侍郎》“千家砧杵共秋声”,韩?所作之《酬程延秋夜即事》“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等。从这些作品中可看到:一是捣衣通常是在秋夜里进行的;二是其旨意大都同征夫怨妇连在一起。 海南本土的诗人们似很少注意到这一题材。笔者搜集的传统崖歌则有几篇直接唱到捣衣,其中一首摇篮曲“硼碰砰,上岭砍柴削稻通; 削得稻通来通布,通青通红给侬捧”。“稻通”也即“杵”,但这种杵的形状和功用与捣米的杵都不同。后者俗称“舂手”,两头稍尖;“稻通”的两端则是平的,呈圆形,直径12至20厘米不等。它被削成细腰,以便可以在握。长约1.5米左右,原本是脱谷粒用的,故称“稻通”。但后来却多用于捣布了。客语方言中的“通”也即“捣”,或撞击。歌中所说的“通青通红”,便是前面讲过的以不同方式染成的两种布色。经典崖歌《织女叹》中也有“布红布青人争爱,侬穿褛褴谁问查”的句子,可见“红”与“青”是过去客语群衣着的基本色调,也是自制布的基本色调。黑色当然算一种,但喜爱它的多属老人,不入主流,故可略去。浆染过的布是耐用多了,但很硬;故如黄雨师所说,要“放在石砧上用杵捣击,使之软熟”。 崖州妇女用于捣布的“砧”,通常是把石臼翻转过来,拿臼底充当。石臼平时用于舂米、捣物。以一整块大麻石凿就,形同一个厚重的巨碗;高约40厘米,口径约60厘米。底径比口径略小,约45厘米;腰径又小于此数。这玩艺很沉,可达几百公斤,看起来笨重而粗糙,但屁股却十分平滑。此效果可不是雕刻得出来,乃是磨砺而成的--说来有趣,客语群常以石臼磨碑;将石碑平躺着固定在十分结实的木架或板凳上,同时在臼腰两侧绑牢了两支约2米长的平行横杠。四条壮汉每边两人抓住横杠抬起石臼,压在碑上来回推动,另有一人不断往碑上洒水。每个石臼“一生”要磨好些碑。碑平滑了,它的底部也平滑了,就这样成为妇人们捣布的最理想的垫具。碑为死人而磨,布为活人而捣--两样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都让石臼那厚重的屁股来承担。 捣布时,把一匹(三丈长、一尺宽)已靛染、上色的新布折成一叠,由一人蹲在屁股朝天的石臼前把握着,平放在临时改用的“砧”上。另有三两妇人手持稻通,站着,轮流向新布撞击,状似捣米。这时,执布者要不时翻动布捆,使它的被撞点尽可能分布均匀。“通布”者一仰一俯,配合默契。口扣着地面的石臼形成一个“共鸣箱”;木质有别的稻通,便在上面撞出节奏感很强的、动听的、不同的音响。此时,常有一帮女孩围观、学习,直至现在,笔者还记得那捣衣的杵声。在魏晋骚客的吟哦和唐宋诗人的清歌里,它是远古的、抽象的、无可捉摸的,但在天涯的月光下,笔者却如此真切如此具体地聆听过它铿锵的律吕,感受过它动人的魅力。而今,这杵声已成为人间的绝响,晚辈们只能从古人的吟咏中,朦胧地领略它的那点飘渺的余韵了。遗憾的是,笔者当年在歌舞团担任创作员的时候,未曾想到过把这项轻松有趣、内涵丰富、诗意盎然的劳动编成一个舞蹈节目,而迄今为止也还没有相关团体把“捣布”搬上舞台。希望有人能就此创作出一个精致的歌舞作品。 衣裳:苦涩的思忆 从纺纱、剥麻和捣布,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捣过的布绵密、柔软而有光泽;捧在手里,主妇们可以酣笑一下了。将布料变成衣服,虽然不像把米做成饭一样容易,但如同做饭较之于种田,制衣比起织、染来要轻松得多,也方便得多。灵活的主妇也可以自制衣衫,但为了缝得更好看些,多数人还是乐意延请专业的裁缝师傅。 彼时没有缝纫机,只能用手工制作。全副工具加起来也不过几斤重,既简单又轻便:有剪刀、针线、衣尺、蜡团、布锤等。蜡团,用于擦线,以免它起毛、蓬松。布锤,只是一块以格木制作、看上去呈等腰梯形的圆柱体,一头大、一头小;大的那头直径约6厘米,小的那头直径约4.5厘米;高约14厘米,其作用是敲打缝合的接口,使之平整。缝衣师傅就拎着这五样东西,脚蹬“槟榔皮?”或“牛皮?”,头戴“打狗笠”,奔走于天涯的乡村阡陌上,以替人缝衣为生。他们的收入是微薄的,有位老裁缝,为人诙谐幽默,会编唱民歌,虽然缝衣手艺出色,但也没有积下什么家财。缝纫机出现后,他的旧手艺随即成了没用的古董,生计就更艰难了。 缝纫机的到来使衣服的制作更为方便、容易,质量也更高。它究竟何时进入天涯?笔者不敢妄断,可以肯定的是直到建国初期,老家才有个别“剪衣师傅”拥有了它。开始是“胜家”牌,稍后则用“华南”牌。在“华南”时代,缝纫机已不那么稀罕,而手工缝衣的历史也就此永远结束了。 与缝纫机相伴而来的是铜制(或铁制)熨斗。这是一个可从上方提着木柄开合的、底部很平滑的铜盒子。把炭置于其中,以刨花或纸屑为“火引”,烧热了,就可用。此间,还得不时给它“喂”炭。小时见过村里一位老裁缝烧熨斗:它摇着葵扇,不断往“铜盒”后端的圆形气孔里送风,而里头冒出的白色浓烟呛得他不断流泪、咳嗽。后来读到力倡宫体诗的梁朝简文帝萧纲《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诗“熨斗金涂色,簪管白牙缠”,始知此类用具之古老。虽不知1500年前的萧纲所吟之熨斗与笔者所见者是否形似,但可肯定二者的原理与作用是一样的。这种炭烧熨斗一直使用到1990年代后期,故乡有了电,后来又出现了电熨斗,它才渐渐被淘汰出局。 其实,“穿”已不再是天涯农村的问题,因为大工业时代的种种发明已使“衣”变得愈来愈易得,而不像“食”那样,仍须以农业为依托。笔者从织染写到捣布,又从捣布写到裁缝。现在,“衣服”终于制成了。 一套成人衣服所用的布料是一匹。崖州乡村自制土布的宽幅为一尺,一匹布的标准长度为三丈,即将近10米。这么长的布可是一丝半毫地积攒起来,又经过靛染、上色、浆捣等多道工序才终于完成的。因此,成衣的艰辛与衣服的宝贵,就可想而知了。对于不同辈分、不同年龄的人来说,这新衣都具有不同的意涵。父母的新衣是做客时才会动用的;等待出阁的女子的新衣是她的嫁妆;小孩的新衣是过年的礼物;未婚小青年的新衣是向姑娘们宣示家道殷实的“广告”--他们可以立马穿上,给头发加点工,哼着崖州民歌招摇过市,以吸引未婚女子的眼球。他当然得像爱惜自己的脸面一样爱惜这衣裳--倘要出恭,须先把裤子脱下来,小心翼翼地托在手里,避免蹲下时把它弄皱了。便是躺在酸豆树下的稻架上闲聊,也得解下新衣挂上树枝,只穿一条“裤?”,以免令新衣受损。虽然“住宅”在“婚姻磁场”中的吸引力较之“食”与“穿”都要大得多,但你无法抱屋同行,也不能总是手执鸡腿作“足食”状,所以,就只能在“丰衣”方面尽量放射“魅力”了。 普通百姓,大抵把衣服分为三类。用客语方言表述之,是谓“看侬褡”、“平常褡”、“做工褡”。“看侬”即做客,通常指赴吃“结婚酒”、“升梁酒”及“对岁酒”等,总之是参与较大型的乡村集宴。这时,就要翻出平时舍不得穿而锁在箱底的“看侬褡”。待赴宴归来,还得脱下来重新藏起。“平常褡”是指半新半旧的那种,用于平日相互串串门、“讲圣谕”,或参加普通的、非正式的社交活动。“做工褡”是穿去“田野园坡”劳动的,是些补了又补的百纳衣,或干脆只是无法再补的“布褛槌”。也有人带着“平常褡”去做工,但他们做工时往往光着膀子,待晚归途中才把衣服穿上。少年时,笔者注意到有位六七十岁的老农下地时就总是裸着上半身,只把一件黑衫象征性地搭在肩膀。他的皮肤被晒成酱色,皱巴巴的像海棠树壳。更为“悲壮”的是一些农民,在劈山开荒时,宁让荆莽把自身划出一道道血痕,也舍不得穿上带去的衣服。因为皮肤划伤了可以自己痊愈,而衣服撕破了却要赔上布片和时间来缝补。 在棉布稀缺、添衣不易的情况下,对衣裳的保养自然也就备受重视。较普遍的做法是用薯粉兑了热水来浆洗;或用“牛皮胶”煲水以浸染。两种作法都会使衣服变得“坚挺”和耐用,但穿起来如同砂竹相磨,??作响。老妇人最喜欢这样做,对褪了颜色甚至打了补丁的旧衣服,可让它在蓝靛中“回缸”--“捏拿”一番后,又变成了“新”的。只是旧衣不似新衣那样容易吸纳“缸靛”,若“捏拿”力度不够,颜色渗得不透,则汗水或雨水都可能把衣服上的“二过”靛青引出来,反把人染成青面蓝皮。少年时代,笔者确乎在雨中遇见过全身蓝靛淋漓、龇着白齿苦笑的途人。那时的感觉是滑稽,现在的回忆是苦涩。 补衣,是女子必修的日课。实在已经破得无法再补,也总还有一两处地方可用。那么,就把它撕下来,当别的衣服的补丁。几乎每家都有一个专用的破藤篮来收容这类布片及旧裳,以备不时之需。这篮子被客语群称为“布褛篮”。因母亲早逝,笔者患病的父亲兼行母责,为几个孩子拾掇破衣。每从初中放学回家,见父亲坐在铺于母亲灵桌前地面的破席上,俯着瘦骨嶙峋的身子,戴一副缺胳膊断腿的破旧老花眼镜,费劲地将补丁缝上衣服的裂口,笔者总不禁泪目模糊。“布褛篮”中的破烂都被扒出来了,他显然是为找到一块合适的补丁而煞费苦心。当时有一句流行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笔者也学会了缝补,对破衣有三种修补方式:通常是让补丁从外头把裂口整个遮住;第二种则是将补丁掇于裂口后面,也即贴在衣服的内里;第三种的“技术含量”最高,俗称“尺狗牙”。“尺”在这里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意即向前行进,如尺蠖状。此法多用于较新而不慎撕破的衣服。它无需补丁,只以丝线勾织成犬齿交错、细密有序的条状网络,像拉链似的将裂口封住。高明的织补者可以弄得天衣无缝;而我在这方面也还算是个“二流选手”。 对于衣着的贫困,崖州客语群有十分精彩、形象、诙谐而又简洁的表述,即七个字“竹竿穿湿人穿渴”。“渴”在客语方言中是“干”的意思,与“湿”相对。洗过的衣服是湿的,晾在竹竿上,是为“竹竿穿湿”。晒干了,人立马穿上。人与竹竿就这样轮流着“穿”一件衣服--它的稀有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还有一首崖州民歌这样唱道:“天公作雨勿作大,沃侬褡湿无褡换;侬只此条褡搭仔,穿又怕湿解怕寒。”在客语方言中,“大”、“换”、“寒”三字的韵母都是“ua”,而“大”、“换”均读平声。“沃”即“淋”。这是笔者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首摇篮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种民生状态。直到1970年代末,这种状态还很难说已经得到根本改善,笔者返乡时看到有的乡亲穿着用进口化肥袋改制的衣服,上面印着“尿素”、“日式株式公社”等字样,不禁百感交集。 好在这一页已经翻了过去,如今,“穿”早已不再是问题。“布褛篮”以及相关的那些描述,都已变成一种苦涩而遥远的思忆了。
上一篇:【文化与旅游】海南走读印象
下一篇:【文化与旅游】蔡明康的三亚民间文化博物馆